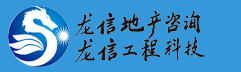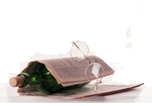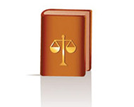| 房價會不會暴跌?這篇深度文章給出了明確答案 |
作者:胡偉俊、彭帥鈞 來源:首席經濟學家論壇(ID:ccefccef) 中國房地產是不是泡沫? 談到中國房地產,許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泡沫。以中國之大,在個別城市出現樓市泡沫當然是可能的。但如果把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看作泡沫,則無法解釋三個非常顯著的事實。 首先,如果房價上漲是由于寬松貨幣所導致泡沫現象,那么我們應該看到房價在大多數城市普遍上漲。事實上,中國房地產市場是個兩極分化非常嚴重的的市場。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的房價漲幅確實非常大。但是大部分城市的房價,過去幾年的累計漲幅其實非常有限。根據搜房的百城指數,中國最大的100個城市里,有62個城市今年9月的房價水平比2013年9月時要低。只有17個城市的房價比三年前高20%以上,而這17個城市去年只占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的16%左右。換句話說,房價長期大幅上漲,并不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。
第二,在大多數市場泡沫中,基本面越差的資產往往價格上漲越多。因為泡沫中的交易主要為了短期買賣而不是長期持有,所以基本面是相對次要的。但上述提到的17個城市,13個城市分布在中國三大城市群,包括珠三角(深圳,珠海,惠州,東莞,中山),京津冀(北京,保定,廊坊,石家莊,天津)以及長三角(上海,昆山,蘇州),剩下四個是地區性中心城市(廈門,南京,合肥和武漢)。換言之,這17個城市都有因人口集聚或中心城市外溢所帶來的基本面支持,這和股市泡沫中,往往越是沒有基本面支持的垃圾股漲的越多不同。
第三,中國房價上漲的分布越來越極端。在上一輪房價上行周期中,大多數城市的房價漲幅居中,漲很多或者很少的城市是少數,整體漲幅呈鐘形分布。但是這一輪房價上行周期中,兩級分化極其嚴重。同樣以搜房統計的100個城市來說,2016年9月的房價和12個月前相比,有22個城市房價超過15%,個別城市甚至超過40%。但同時也有63個城市上漲小于5%。漲幅分布從上輪的兩頭低中間高,變成了兩頭高中間低。泡沫理論同樣無法解釋房價漲幅的分布在最近兩輪周期中的變化。
不是泡沫那是什么?土地的供需錯配 在房價加速上漲的時候,比如2013年或今年,很多人看到的是高房價,所以認為房地產是“泡沫”。但當房價下降的時候,比如2012年和過去兩年,人們看到更多的是高庫存,所以認為房地產已經“過度投資”了。事實上,中國房地產真正的問題在于房地產在地區間的供需錯配。 具體來說,房屋供應和人口流動的方向是相反的,或者說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是背離的。過去5年里,從住宅的施工面積來看,三四線城市的增速遠超二線城市,而二線城市又超過一線城市。后果就是,在人口流入、房屋需求比較大的城市,供應是不足的,因此房價長年上漲。而在人口流出、房屋需求比較小的地方,供應是過剩的,因此庫存高企。 如果因為出現庫存問題就認為中國房地產是過度投資,那么合理的政策就應該是降低全國范圍的土地供應。例如今年上半年,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,住宅土地的成交面積就在“去庫存”的名義下,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70%和51%。但如果供需錯配是正確的,那么不應該采取一刀切限制樓市的政策,而應該在供應不足的城市增加供應,而在供應過剩的城市減少供應。否則,供需不平衡在未來將進一步惡化。
供需錯配和泡沫:截然不同的含義 供需錯配和泡沫,都可以表現為房價高速上升,但兩者是不同的。 首先,兩者的本質不同。如果北京今年只拍賣一幅土地,這幅土地的價格一定是天價。但這是因為供應不足而非泡沫造成的。對付泡沫的辦法關鍵是管住需求,但用同樣辦法來對付供給不足,短期也許能壓住房價,但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,更可能惡化長期的供需平衡。 其次,對于房價判斷不同。供需錯配的情況下,一線城市也會由于政策打壓和需求透支,出現短期房價見頂并下跌的情況,但市場能在比較短時間復蘇。如果是泡沫破滅,就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復,比如香港97年和美國07年房價泡沫破裂,分別用了15年和8年才回到泡沫破裂前的水平。所以一個人對未來房價的判斷,以及是否作出購房的決定,和他認為目前房價是否是泡沫密切相關。 第三,經濟預測含義不同。如果是泡沫,總有破滅的一天。從其它國家的經驗看,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幾乎毫無例外會伴隨著經濟長期低迷,不太可能很快復蘇。但如果房價漲主要是因為供需錯配,那么在政策壓力和需求透支的情況下,明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確可能進入下行周期,中國經濟當然也會受到負面影響,但不太可能出現房地產泡沫破滅后的大蕭條和長期停滯的景象。 第四,驅動因素不同。供需失衡和泡沫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杠桿率和短炒的比例。中國的一線城市既有限購,又有限貸,首付至少20%,而且短期買賣的稅費成本非常高,這一切都使得資金快速進出的難度很大。至于本地市民由于擔心房價上漲提前購房,這更像是透支未來的需求而不是炒房,這一點從政策收緊的時候就能看出來。如果是泡沫,當政策轉向的時候,通常會出現投機客紛紛出逃卻無人接盤的情況。但中國每次收緊樓市政策,我們看到的,更多是購房者試圖在政策收緊前趕上最后一班車。相比樓市,土地市場沒有限購等進出限制,而且開發商的杠桿可以遠高于購房者,出現泡沫的可能性要大不少。 最后,需要強調的是,不是泡沫,不代表合情合意。我們將在后文中講談到,由于土地供需錯配所造成高房價與高庫存并存,既不合情(財富分配)也不合理(經濟增長),但并不能因此得出高房價就是泡沫的結論。 關于房價的其它解釋 關于房價還存在著其它的解釋,例如貨幣超發或者人口結構。這些解釋都有其合理的部分,但是相對于土地的地區供需錯配,都是相對次要的。 例如,貨幣超發無法解釋中國大多數城市的房價漲幅非常有限。而且,金融危機之后,全世界央行都通過貨幣寬松刺激經濟,但大多數國家的房價并沒有出現如中國一線城市這樣的大幅上漲。此外,香港由于匯率同美元掛鉤,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。但房價仍然長年很高,所以關鍵還是供應問題。 事實上,房價和貨幣是互為因果的。很多人覺得政府刺激樓市,就是央行嘩嘩開動印鈔機,老百姓手上錢多了,就把房價買上去了。其實,更加符合現實的描述是,樓市升溫,房地產成交量上漲,導致房貸上升。當這些房貸被開發商或賣房人存到銀行后,就變成了存款,而存款就是貨幣。另外,房價的上漲,會導致了房產和土地作為抵押品的價值上漲,從而可以撬動更多的貸款,這些貸款最后也變成存款。 換句話說,樓市火爆導致了貨幣增速的加快。所以,不能因為貨幣和房價高度相關,就認為是貨幣超發導致房價上升。反而更應該問,為什么中國樓市的火爆為什么屢澆不滅?答案正是供需錯配。這也是為什么世界上其它央行也放松貨幣,但房價上升遠遠小于中國的原因。 至于人口結構這樣的慢變量,在發達國家和房價都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,日本90年代房價下跌和美國00年后的房價上漲,和人口關系都不大。至于象中國這樣處于劇烈的結構轉型的國家,人口的影響就更加模糊。中國勞動人口(15-59歲)在2010年左右就已見頂,但之后房地產市場仍經歷了兩輪周期。上海2015年人口是下降的,但2016年卻經歷了房價的大幅上漲。而且,全國層面人口結構的變化,也無法解釋中國房地產市場為何變得如此兩極分化。 而且,中國的人口流動遠未完成。由于現存的戶籍和土地制度,雖然農業只占中國經濟9%,但農村人口仍占中國人口的44%。目前以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僅56%,而以戶籍計算的僅40%,遠遠小于歐美和東亞國家超過80%的城鎮化率。同時,中國城市人口內部的遷徙也遠未結束,由于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,中國一直存在大城市太小,小城市太大的問題。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的居民占全國人口的比例,要遠遠小于大多數國際的一線城市。同時,地區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之大,也是國際少見的。所以,人口將繼續向大城市及其周邊城市流動,甚至在每個省內部,人口也正在向省內的一線城市集中,像河南,遼寧和安徽這樣的人口大省,過去五年省會人口的增加都超過了整個省的人口增加。
供需錯配的背后:土地制度 土地在地區之間的供需錯配,導致了部分城市土地供應不足,房價高速上漲。而大部分地區土地供應過剩,庫存高企。而在這背后,正是中國特有的土地制度。 對于中央政府而言,房地產是穩增長重要的政策工具。房地產及其相關行業,占經濟的比例要超過20%。對于存在增長目標硬約束的中央政府而言,自然無法坐視房地產持續低迷。從1998年的房地產市場化改革,到2008年四萬億時出臺的樓市政策,再到今年2月的下調首付比例,背后無不具有穩增長的考慮。 另一方面,出于社會輿論的壓力,政策制定者也無法坐視房價長期快速的上漲,必須出臺政策調控樓市。這種糾結的心態,造成了中國樓市另一個特有的現象:短周期。當樓價下調一段時間,政策就會出臺刺激樓市。當樓價上漲一段時間,政策就會收緊來打壓樓市。所以,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中國的香港地區,房地產通常會經歷持續多年的長周期。但中國過去十多年內,就已經經歷了4-5次房價短周期,背后都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在起作用。
對于地方政府而言,土地的作用更是三位一體的:既是財政收入的來源,又是貸款的抵押品,還是招商引資的政策工具。 一方面,賣地收入和與房地產相關的稅收收入,有時會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。另一方面, 地方政府通過將土地注入融資平臺,然后用土地作為抵押品,可以通過杠桿來撬動更多的資金從事投資。而這些投資能帶來更多更好的基礎設施,從而使土地進一步升值,帶來更多的資金。這樣的良性循環是中國過去20年經濟奇跡的重要一環,也是地方政府經濟學的重要一課。最后,地方政府也可以通過土地優惠來招商引資,從而帶動本地就業和稅收的上升。 對于大城市,由于擁有多種產業和政策工具,不論在資金和招商引資上,對土地的依賴度沒有中小城市那么大,而且有控制人口的目標,因此土地供應相對有限。而中小城市由于財政資金有限,對土地的依賴度更高,這就導致其土地供應過大。但是人口又是從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的,這就出現土地在地區間的供需錯配。 以上海為例。上海的城區面積在6300平方公里左右,但其中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只有大約一半。其他的土地大部分是農業用地,但農業占上海經濟的總量已經不到0.5%。在城市建設用地中,工業用地將近30%,遠遠超過世界上大多數一線城市,例如香港的工業用地僅占其城市用地的10%。 同時,上海的耕地面積大概在1800平方公里左右,但在2015年的住宅類土地的成交面積卻僅有7平方公里不到,并且逐年下降。而且這些成交的住宅類土地,平均容積率只有1.8,遠低于國際一線城市5-10的水平。目前來看,上海的土地供應受到了國家建設用地指標和耕地紅線的限制,增加的空間相當有限。但是在整個中國經濟的層面,一方面在人口流入的一二線城市保留大量耕地,另一方面卻在人口流出的三四線城市將大量耕地轉為住宅用地,造成大量庫存積壓。這種土地在地區之間的供需錯配,產生了土地和勞動力配置效率的下降。
樓市的風險有多大? 討論了房地產市場背后的影響因素,回到當下,一個重要的問題是,給定部分城市的樓市火爆,接下來房價大跌,并導致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有多大?我們認為,樓市重演去年股市崩盤,或者美國08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并不大。本輪地產周期仍將重復之前幾輪周期的情況,在今年需求的提前釋放以及政策的打壓下,明年房地產市場可能進入一輪新的下行周期,成交量和價格都將逐步趨冷。但是,如果目前的土地供需情況不改變,面對人口流入的一二線城市,中長期來說住房仍會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況。 首先,前面已經提過,中國的城市中,樓價長期上漲的城市并不多。的確不少二線城市今年漲幅很大,但也要看到,這些城市之前大多經歷了長期的房價停滯。如果以五年的長度看,房價漲幅很大的仍然主要是一線城市。而一線城市的問題在于供給遠遠小于需求。由供應不足帶來的房價高企,很難說是泡沫,更談不上會破裂。而大多數供應過剩的三四線城市,長期來看房價漲幅非常有限。 第二,中國家庭部門的杠杠率不高。雖然今年房貸的增速非常快,但中國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仍然不到40%,大概23萬億人民幣左右,其中大部分是房貸。假設這些債務的平均利率是5%,每年利息支出 在1.2萬億左右,而居民的銀行存款就有將近60萬億。而且,這5%的平均利率還有很大的下調空間,目前香港的房貸利率就只有2%左右。 第三,中國房價和金融市場的關系并不那么緊密。很多人以為美國08年金融危機的主因是房價下跌,其實,房價下跌只是一個導火線而已。更重要的是,下跌的房價導致了大量以房貸為基礎的衍生產品出現了違約,從而引發金融市場出現大規模恐慌,最后升級為一場全面的金融危機。單單房價下跌本身,并不足以直接導致08年這么大的危機。例如香港在2003年的時候,房價曾比97年的高點下跌了70%,但金融體系仍然正常運作。在中國,類似的房貸衍生產品幾乎不存在。而且中國首付比例非常高,直到去年9月前仍要求30%的首付比例,現在仍有20%,并不存在美國式的次貸現象。 第四,中國政府的房價調控降低了樓市的風險。歷史上幾乎每次房地產短周期背后,最重要的因素都在于政策的變化。中國房價的上升周期通常低于兩年,除了開始的醞釀期,以及最后的熄火期,中間房價上升較快的時間,只有1年左右。上升周期后,再進入一到兩年的房價平臺期,消化前期的房價漲幅。這種沖刺和修整交替的短周期特點,防止了房價在一輪周期中上升過多。10月以來房地產政策再度收緊,樓市已經開始降溫,明年甚至可能出現全國范圍房價下跌的情況。這種短周期的現象,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價格一次上漲過多的風險。 第五,中國政府手中擁有大量的政策工具。例如,由于農村土地產權的性質,中國政府對于土地供應的保持著非常強的控制能力。在樓市低迷的時候減少供地,在樓市火熱的時候增加供地,從而改變供應狀況并且穩定市場預期。事實上,政府不僅可以改變未來的土地供應,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可以改變過去的土地供應,比如從開發商手上回購土地,或者改變土地用途及容積率等。政府還可以控制信貸,包括首付比例,按揭利率,貸款資格等。政府還可以改變購房條件,例如戶籍,居住年限,已購套數等等。 第六,一線城市的限購,使得北上深的房價,主要受改善性需求而非炒房推動。固然在這波樓市上漲中,有大量的購房者加杠桿買房,但高額的交易稅費,使得這些買賣更接近未來需求的提前釋放,而非在短期內的炒樓行為。另外,限購的存在,能夠使得潛在購買力在未來逐步釋放。在大多數市場上,當預期達成一致,比如所有人都看漲時,市場離反轉通常就不遠了,因為這時潛在的買盤力量已近耗盡。但一線城市的樓市不同,即使所有人都看多一線樓市的房價,場外還有大量因限購而無法入市的潛在購房者,買盤的力量依然存在。而且,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本地樓市的狀況了來調整限購條件,從而保證了新購買力長期穩定的入場。 第七,中國作為趕超型國家,在接下來的十到二十年里,經濟增長雖然不太可能重復過去的經濟增速,但仍可能比其他發達國家的要快。這會影響到合理的房價收入比,由于租金是收入的一部分,也會影響到房租收益率。以房價收入比為例,當下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,的確要遠遠高于世界上大多數一線城市。以上海目前的平均收入,普通家庭買房要32年,而東京只需要23年。但是,假如上海未來20年可以保持5%的名義收入增速(包含了通貨膨脹的收入增速),而東京只有2%。那么,上海現在的房價相當于未來20年里每年平均收入的18倍,而東京是19倍。當然,這樣的計算是比較簡化的,因為還需要考慮其它因素,比如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給一線城市帶來的教育養老“租金”,嚴控大城市人口的人口政策,在大城市保留大量耕地的土地政策,以及持有房產的成本差異如房產稅等。
土地供需錯配的負面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,作為經濟研究者,我們主要著眼于預測的準確性而非價值判斷。雖然我們認為樓價大跌的可能不大,引發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更小,但這不代表我們認為房地產的現狀是健康的。就如同我們在“中國債務的虛與實”(鏈接)中對中國債務問題的分析,中國出現美國08年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并不大,但是債務卻折射出中國經濟深層次的體制性問題。危機的可能性低,反而會降低解決問題的緊迫性,長期來看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。 首先,土地的“供需失衡”造成了地區和城鄉之間的財富分配惡化。一個上海居民,和一個長沙居民,還有一個在城市不擁有房產的農民相比,過去10年中財富的變化有天壤之別。雖然他們的工資收入也有差距,但這種財富的差距,主要是由于房產增值帶來的。 其次,土地的“供需失衡“降低了中國經濟潛在的增速。中國經濟越來越依靠服務業和創新,而大多數的高端服務業都位于一二線城市,而絕大多數創新也是在一二線城市完成的。由于房價高企,妨礙了人口集聚的進程,目前北京上海人口的增加速度,和5年前比已經大幅放緩。另外高房價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,也對企業的競爭力產生了不利的影響。 第三,新房價格中可能有超過一半歸政府所有,包括地價收入和稅費收入,這本質是一種從居民到政府的轉移支付。而居民為了買房,則被迫減少消費增加儲蓄。最后的結果是,中國經濟中消費的比例遠低于絕大多數國家,所以儲蓄率特別高。而這些儲蓄最后又通過銀行貸款,變成了投資和債務。這就是我們在“中國債務虛與實”中提到的,中國高債務的根源之一。在這個意義上,中國經濟的幾大重要問題像債務和地產,都是密切相聯的。 保匯率還是保樓市? 目前有一種說法是保匯率還是保樓市。持有這種看法的人認為,因為房價已經漲了這么多,那么中國的房產作為一種財富,已經大大升值,如果人民幣對美元不貶值,那豈不是可以把全世界都買下來?這種說法并不準確。 首先,就像前面提到,房價大幅上漲不是一個全國的現象,過去三年里,房價累積漲幅超過收入累積漲幅的城市并不多。其次,房價代表的是最近成交的價格。而房地產市場是個存量遠超交易量的市場,用當前的交易價格乘以整個房產的存量來計算財富升值,并不合理。第三,即使房價上漲導致財富大幅上升,對匯率會產生一定壓力,但匯率是由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,并不是說財富上升就一定會貶值。就像銀行存款從2000年左右的10萬億人民幣增加到目前的接近150萬億,很多人在多年前就擔心高儲蓄像“籠中虎”,會引發高通脹或大貶值,但至今也沒有發生。 事實上,房價和匯率同向或反向變動的情況都很常見,原因在于,房價只是影響匯率的諸多因素之一,匯率也只是影響房價的諸多因素之一,兩者并不存在一一對應關系。其它因素像資本流動,風險偏好,經濟增長,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,都會同時影響到匯率和房價。最后的結果取決于眾多因素的總和,并不確定。 比如像韓國和俄羅斯這種房價上漲和貨幣貶值同時出現的情況,背后的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比較高,“票子毛了”,所以房價上漲和貨幣貶值同時發生,并不存在匯率和房價的棄保問題。中國2014年前有大量資本凈流入,房價上漲的同時匯率升值。目前,影響人民幣的關鍵在于匯率預期,如果人民幣大幅下跌,貶值預期惡化,大量資本流出,這時恐怕匯率和房價一個都保不住。當然,今后如果人民幣貶值預期可以逐步化解,中國的資本凈流入重新轉正,匯率和房價出現像2014年之前的同步上漲,也不是不可能的。 房地產市場的未來 判斷房地產市場的未來,關鍵看目前的土地制度,戶籍制度,以及嚴控超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,是否會發生松動,因為這牽涉到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核心問題,也就是土地的地區供需錯配。 如果要判斷目前的政策框架是否會發生改變,首先要對在現存條件下的房地產市場發展潛力有所評估。我們測算,截至2015年底,中國的存量住房達到190億平方米。以現在7.67億城鎮人口計算,中國的城鎮人均住宅面積為25平方米。 未來的房屋需求主要來自城鎮化,更新和改善性需求。整體看房地產的增長潛力已經大幅下降。具體來說, 城鎮化需求:中國的城鎮化率在2015年達到56%。假設城鎮化率在2026年達到65% (過去十年從44%增加到56%),這意味著未來十年城鎮人口需要增加1.7億人。假設人均住宅面積為25平方米,這意味著43億平米的新增住房需求。 更新需求:在現有的190億平米存量中,有37億平米是2000年以前建造的。由于中國的商品房市場從2000年初才開始真正起步,在此之前建造的房屋大都質量較差。因此,我們假設其中有一半將在未來十年內拆遷重建。這又將帶來約19億平米的住房需求。 改善需求:以65%的城鎮化率計算,到2026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將達到9.37億人。如果假設人均住宅面積從25平米提升到30平米,這又將帶來47億平米的額外住房需求。 把這三部分相加,未來十年的住房總需求大致在108億平米左右。從新開工的角度看,考慮到目前還有30億平米左右的庫存,未來10年的新開工總和大概在80億平米左右,和過去6年的新開工總和差不多。 以上的估計無疑非常粗略。比如,如果未來城鎮化更多是靠城鄉合并,那么上面的計算就可能會高估需求。其目的不是預測,而是為了一個大致的估計。但似乎可以說,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,房地產繼續大幅增長的潛力是非常有限的,而房地產保增長的能力也將逐漸下降。而且,未來的新增需求很可能集中在人口流入的一二線城市,而這些城市目前面臨著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。所以從長期來看,目前政策框架下房地產長期需求并不樂觀,再加上供需錯配這樣的結構性扭曲,有可能會倒逼目前的土地和戶籍政策在未來發生變化。 債務和房地產的本質都在于要素錯配 本文的核心結論是中國房地產的主要問題并不是泡沫,造成高房價和高庫存并存的主因是土地的供需錯配,而背后又是中國特有的土地制度。由于存在政府的調控,樓市崩盤的風險并不大,但目前的房地產市場已經帶來了諸多的負面影響,不僅惡化了財富分配,也降低了中國經濟長期的潛在增長率。 事實上,房地產和另一個熱點問題債務一樣,具有深刻的歷史和制度背景,反映了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。一個認識的誤區是將中國的債務和房地產問題同發達國家相類比,認為主要風險在于債務危機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。但我們認為,出現危機的風險其實不大,債務和房地產真正問題在于背后反應了生產要素錯配,這種錯配會大幅降低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,這才是最大的風險所在。 換句話說,將中國的債務和房地產問題和美國的類似問題相提并論,就好像兩個人都發燒,但一個是因為肺炎,另一個是由于傷口感染。如果只看體溫高低,把傷口感染當作肺炎一樣治;或者只顧把體溫降下去,不管發燒的真實病因,都無法解決問題。 中國經濟在過去15年能夠實現大幅趕超,要素配置的改善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全球化的大浪使得數億農民離開農業,進入工業和服務業,這種部門之間的勞動力重新配置大幅提高了生產效率。但是,最關鍵的生產要素,包括資本,土地,勞動力,目前仍然存在著嚴重的錯配。 中國的債務問題本質是資本的錯配。在“中國債務虛與實”中,我們談到中國債務主要是國有部門的問題。在企業債務中,國有企業的債務占到6成以上。國有企業債務加上政府債務,占到中國總債務的65%。由于債主也是國有銀行為主,再加上政府的干預能力很強,短期爆發債務危機的可能不大。但是,對危機風險的過度關注,可能會忽略債務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,也就是資本在國有和民營之間的錯配。一個表現就是中國民營企業的規模有限。在2015年財富500強中,有94家中國企業入選,僅次于美國的128家。但美國公司基本都是民企,而中國的94家企業中僅有9家民企。如果不解決債務背后的體制問題,光通過一些財務手段降低賬面債務,并不能真正達到去杠桿的目的。 而房地產市場則是土地的錯配。一方面人口流入的大城市保留大量耕地,造成房價高企。而另一方面人口流出的城市建造了大量住宅,造成庫存堆積。將一線城市的房價大漲,同其他國家歷史上的房地產泡沫對比,無疑忽略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在供給端的巨大問題,并對一線城市房價的長期走勢產生誤判。 最后,戶籍和土地制度也造成了勞動力的錯配。這既存在于城鄉之間:雖然農業占中國經濟的比重已經低于10%,仍有超過40%的人口住在農村;也存在于城市之間,原因正是上面提到的土地錯配。 因此,將中國經濟同日本90年代簡單類比,認為中國將面臨“失去的二十年”,這種比較并不準確。日本90年代并不存在如此巨大的土地,資本和勞動力的錯配,當然也不存在由于糾正這些錯配帶來的增長潛力。但中國能否釋放這些潛力,關鍵在于改革。真正解決中國的債務問題,主要在于國企改革,改變資本在國有和民營之間錯配。而真正解決房地產的問題,主要在于土地戶籍以及相關的財稅改革,讓土地的城鎮化跟隨人的城鎮化,而不是相反。在這個意義,債務和房地產作為近年來最受關注的兩大問題,既體現了中國經濟深層次的體制問題,也蘊含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抓手。 來源:漫步金融街   |
|
上一篇:1/3房企布局租賃市場 長租公寓將是“香餑餑”?
下一篇:公積金異地轉接平臺本月上線 [返回] |